 |
創意之道─龔大中 城市綠洲,一位漫行者─吳東龍 解讀字的表情─漢字字型設計進行式 極地探險─Hunting for Northern Lights 藝術,做為時代的提問者─《徐冰:回顧展》專訪徐冰 設計師,充電中─馮宇市場才是真正的戰場 |
藝術,做為時代的提問者─《徐冰:回顧展》專訪徐冰
徐冰現任中央美院副院長,是中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其以漢學為底蘊,融合文字、版畫、觀念藝術、行為藝術、裝置等多樣手法,呈現出當代藝術的新貌,此次於北美館首度推出個人大型回顧展,徐冰與我們一同回首他的40年藝術旅程。
【文/彭永翔;攝影/汪德範;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攝影/汪德範)

蠶花與蠶系列作品之〈在美國養蠶系列三:開幕式〉,放置數百隻蠶於桑樹枝上,就在桑葉逐漸被啃食的過程中,有些蠶死亡了,有些則順利吐絲繭化,生命的風景與改變,清楚表達於這件作品中。(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與蔡國強、谷文達、黃永砯齊列名為中國實驗藝術四大金剛的徐冰,現任中央美院副院長,是中國當代藝術發展中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他以中國文化、漢字為底蘊,從〈天書〉、〈英文方塊字書法與教室〉至〈地書〉,自〈五個複數系列〉、〈蠶花與蠶系列〉至〈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概念間的挪用、轉換,以作品中的時間及過程性表達人世無常、社會轉變;橫跨版畫、觀念、裝置、社會研究及行為藝術,徐冰的作品不被風格所侷限,始終以各樣手法回應當下時代與環境所產生的議題,如同他所說的「好的藝術家懂得去處理它與時代中的關係,有處理這樣關係的本事」。徐冰也不斷以其作品向世界叩問,質疑社會主義、質疑資本主義、質疑世界,以藝術發聲。
La Vie:你的許多作品以版畫作為媒材,你對於版畫的興趣是始自於趙寶煦先生提供相關書籍給你開始嗎?對你而言,文字及版畫的魅力為何?
徐冰(後簡稱徐):對版畫的興趣與從小跟父母、北大教授、趙寶煦先生都有關。小時候喜歡畫畫,當時又沒有太多資訊,所以美術、繪畫的來源都是當時的報紙及雜誌封面封底。我父親會整理辦公室的舊雜誌、或是父親同事會把封面、封底撕下來交給我,我再把它剪貼成畫冊,當時因為印刷術效果不好,中國在雜誌發表的作品絕大多數是版畫,版畫跟現實生活有非常緊密的聯結,所以我對版畫很有感覺。
La Vie:從〈天書〉到〈地書〉皆似乎有意挑戰馴服於僵硬的文化思維,是你創作的本意嗎?從早期的以不溝通刺激溝通,到後期更為親近大眾的嘗試溝通,可以請你談談這其中的心境轉變?
徐:創作〈天書〉時很希望自己的作品像當代藝術,可能是因為那時太沒有藝術了,以為藝術就是這個樣子。〈地書〉則是因為我參與了許多當代藝術國際化的活動後,發現當代藝術的問題:因為我始終不喜歡把藝術與當代藝術、把當代藝術與一般人區隔開來,例如很多作品喜歡先把人給嚇跑,所以我嘗試讓作品很親近,大眾化。
創作〈天書〉時,中國大陸那時強調藝術來自於生活,而我正開始反省這樣的關係,想找到一種藝術的新方法。但走過之後,我們發現〈天書〉實際上卻是一個來源於生活的作品。
因為當時中國大陸正在文化熱的關係中,大家對於文化都有一種新的渴望、追求與期待,〈天書〉與當時的環境非常有關係。天書並沒有遵循西方藝術發展的框架與方法,而是滋長於自身傳統文化與現實語境的作品。
回過頭來看自己的作品,雖然原來想做一個國際化的當代藝術家,但幫助你的卻是這些背景的滋養。我們怎麼用我們的傳統文化,從背景中尋找養料,就是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如何激活、挪用、轉化等。

〈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讓印滿偽英文的公豬與偽漢字的母豬現場交配,不僅反映時代,也產生出文明與自然的兩相對照。(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La Vie:你的作品總是回應著時代與當下環境,且不拘於風格限制,藝術養分源自於藝術之外,對你而言,一個好的藝術家是否需要具備這樣的特質?
徐:藝術源於生活的理念,我越做越覺得它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我發現藝術的高下與深度並不來自於風格,它比較不出好壞、無所謂好壞,但是好的藝術家懂得去處理它與時代中的關係,他有處理這樣關係的本事,這個本事就有高下之分。
好的藝術家首先是非常具有思維能力的人,對這個時代的核心非常敏銳,像Andy Warhol,你可以不喜歡他的作品,但你不能否認他對於5、60年代美國的文化核心認識最深刻。藝術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影響了他的生活方式、藝術創作的方式,Andy Warhol就做了一個很好的關係處理。而齊白石很懂得中國傳統與所身處的時代如何發生關係,他的作品為什麼有意思,因為他有文人畫的深厚傳統,同時因為他出身於底層,所以他對於這些現實生活中零碎的東西非常有認識、有興趣,而這正是當時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對於大眾關注的結果。
或是像〈地書〉不可能在25年前發展,因為當時尚未國際化,符號、icon的發展並未普遍,不會有〈地書〉的發展。如果今天才創作出〈天書〉,也很奇怪,因為關係就不對了。藝術在一個特定文化上下文的關係中才具有意義。〈地書〉為什麼在今天出現,是因為〈地書〉的材料現在才有、現在才出現。
La Vie:一般寫作時我們有著思緒流動,這本〈天書〉結構完整,當你將這4,000多個假字以活字印刷排列組合成〈天書〉的思考脈絡是什麼?
徐:創作〈天書〉時,其實是為了逃避文化熱的困擾,期望找到一個關係讓自己感覺很踏實,當時的滿足就在於每天刻了幾個字的積累。那些字我是依照康熙字典的筆畫順序來造字,把不同的偏旁結合,再從中挑選我認為最像漢字的字,所以在這4,000多個字中,就有筆劃少到筆劃多的各種造字。

〈天書〉是徐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試圖以「完全不溝通來刺激溝通」,以不溝通撼動對於中國傳統的反思,在當時更引起了中國藝壇廣泛的多面向討論。(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La Vie:一個口字裡面有正字標記的意義是?
徐:那是數字,謝謝你啊,你關注得很細。一個正字就是五,據有數字的意義,用以標注頁數、章節、目錄,這個書雖然沒有內容,但內在結構與章節的規範非常嚴格,所以前面的目錄是對到後面這些符號。而這一段為什麼要停、要補註釋,其實是有根據的,實際上我是根據過去的某一本書的某一段落來編排。
La Vie:〈五個複數系列〉、〈蠶花與蠶系列〉、〈背後的故事〉等,「過程性」及「概念的轉換」以不同方式呈現於你諸多作品中,為何採取這樣的手法?
徐:我的作品其實總是在概念與概念間做文章。比如說英文方塊字,它像字卻又不是文字,〈天書〉像書又不是書,概念之間的界限就開始模糊了。
而我有興趣的是一個東西慢慢的轉換,成了不一樣的東西,總是不確定,而你又不知道它在哪一個環節產生轉變,像是一個寓言。就像〈五個複數系列〉從黑的什麼都沒有到白的什麼都沒有。
La Vie:似乎你對於時間的議題、人生或大環境的改變、都會以不同的手法去呈現?
徐:確實是有這樣的內容,像我其中一件作品叫〈轉話〉。其實我的東西總是在探討文化與人類的關係,所謂文化就是人類從我們的實踐中不斷總結出來的東西,給它規定為一種知識。成為知識的東西一定有一個邊界及明確概念,中文的一個字就是一個固定的符號、固定的概念。但這與人類的關係究竟是什麼,我很有興趣。
而現實生活中有許多是無法被歸類為知識與概念的東西,而往往對我們思維有推進的就是尚未形成概念與知識範疇的內容,哥倫比亞大學的劉禾教授也總是認為我的作品在觸碰理論與知識範疇的前沿課題,而那也是尚未被歸納為概念與知識範疇的理論。真正有探討價值的都是那些不確定、鮮活的、模糊的,我們還不清楚的東西。
La Vie:過去你曾經做了〈緩動工作平台〉(Slow Moving Ergodynamic Desktop)這類融入於生活中、看似與設計及科技相關的創作,最近還有做其他此類作品嗎?
徐:這段時間比較沒有。那個時候對科技與生活很有興趣,最主要是對於當代藝術領域範疇的貧乏和不滿,所以想從其他領域獲取。比如說木林森這個項目也是環保的,用藝術來嘗試解決人類的環保議題;而〈緩動工作平台〉是從科技切入,談的是電腦科技對於人類的損害;〈菸草計劃〉則是就歷史與經濟切入,像是社會學研究,又像是藝術家的呈現。

〈大輪子〉及〈鬼打牆〉都是將「實物的痕跡轉印」擴大的作品。(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La Vie:〈地書〉對於科技是比較中性的表述,〈漢字的性格〉則較反科技,科技發展、資本主義與生活間的關係?
徐:科技是最根本左右人類文明的動力,包括書寫風格的演變,從刻字、寫在絹上、寫在紙上到硬筆、至現在不寫變成打字。中國用軟筆書法、方塊字,是我們的性格、文化,中國人思維的靈活性及隨機應變性與我們的書法文化是有關係的,書法的第二筆是根據第一筆來,第三筆是根據前兩筆而來,最後一筆調節平衡,中國人很善於在一個臨時的條件下,思維我下一步該怎麼辦。
但是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進入後,我們加入了許多計劃性、規定和測試,之後我們再去工作,沒有人沒有車我們也要等紅綠燈,這是理性、是好的。
文字作為功用性,它怎麼方便就怎麼發展,打字一定戰勝書寫、硬筆一定戰勝軟筆,因為它更方便,這是文字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為它不考慮文化發展性及美感。但是書法文化現在就有一個危機,不僅僅是不寫書法、不寫字,幾代下來,它會改變這個文化的核心基因部分,會讓我們的文化特徵趨向於西方化、無特徵化。
我有一種願望,為這個大的文化去提供一種缺失的東西。過去的1、200年是以西方文化為主軸。現在毫無疑問的顯示西方文化的疑問與弊病,在北京生存很有體驗,連呼吸都有問題。這些是誰帶來的呢?是資本主義家帶來的,還有為什麼有這麼多戰爭?
人類有不同階段,必須成長、發展不同領域,年輕時談戀愛要發展浪漫的情懷,這是法國人所擅長的;也過了積極賺錢的資本主義壯年時期,而到了五十知天命的時期。在壯年時期我們不斷地積極工作,想要改變這個世界,但你越想要改造,才發現離最後的理想目標越遠,就像人50歲時,就知道天命的重要了。
人是必須要知道天命的,天命是什麼?是你怎麼尊重自然、與自然配合而不貪婪地跟隨自然生活,這種世界觀是中國文化最懂的。顯然人類的文化重心一定要轉到這樣的世界觀文化地帶,這就是我們藝術的最終價值與基石。
La Vie:所以《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實現》是你心中的桃花源實現嗎?
徐:它是啊!當初我到V&A(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看,看到這圈湖水,我就覺得它很珍貴,因為它是被歐洲古典四四方方的人工建築所包圍,在倫敦這個最代表西方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城市裡。由於人類在這個大院子外的問題,會讓我覺得這湖水特別珍貴。
La Vie:下鄉、1990年時移居美國,之後回國擔任中央美院副院長,這三個階段對你創作的影響是什麼?40年來你覺得對你的藝術發展最關鍵的時刻?
徐:其實很多時期都是關鍵,沒有去插隊可能就上不了美術學院,插隊、上美術學院、至美國我想都是關鍵。其中插隊後讓你了解這個國家核心的問題,它與政治鬥爭的環境形成非常明顯的對比。在文革時,北大是重災區,我家自然也受到牽連,當時你體會的人際關係是另一種;你到農村時,離自然很近、政治很遠,你反而更能體會政治間的關係。
La Vie:從以文字為脈絡的創作、以物質形構視覺轉換體驗的《背後的故事》、《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實現》、《何處惹塵埃》、直接挑釁的《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至參與社會行動的《木林森計畫》,你如何觀察這多年來自身藝術創作的變與不變?
徐:不變的是內在的藝術方法與性格,變的是世代在變,所以作品也跟著變。內在的藝術方法就是人的性格,是張揚或是內斂,你是這樣的性格,一定會影響作品的結果,這圖形你讓它尖銳些或含蓄溫潤點,都是與你的性格有關,這是不變的。
La Vie:平常創作時感到焦慮嗎,你會如何面對處理這樣的情緒,再繼續進行創作?
徐:我焦慮的時刻是幫別人題字時,我前兩個字寫得特別好,第三個字我就會焦慮,因為我怕第三個字寫壞了,前兩個字就浪費了。這其實與你的境界有關,你的境界如果真的高,就不會焦慮了,我的境界不夠高,我才會焦慮,因為我仍在計較得失。至於藝術創作的焦慮比較沒有,因為藝術創作比較是一個自然的結果。
La Vie:目前有正在其他發展中的創作能與我們的讀者分享嗎?
徐:雕塑作品〈鳳凰〉會逛到紐約的聖約翰主教堂;之後3、4月木林森在史博館會有展覽,屆時會有一個比較大型的創作,把孩子的畫拼成一張大的森林山水畫。
徐冰
1955年生於重慶,1981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1990年接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邀請,以榮譽藝術家身份移居美國,長期活躍歐美,是國際藝壇極為重視的當代華人藝術家。2007年起返回中國任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並曾榮獲1999年美國的麥克阿瑟「天才獎」、威爾士國際視覺藝術獎(Artes Mundi)等。徐冰認為「藝術家像是作品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傳達體」,每個藝術家將自己特殊的部分通過作品帶入藝術界,讓人們的認識有所啟發與推進。
完整內容請見LaVie2014年03月號
【更多精采內容請上《LaVie 設計美學家》;《La Vie 設計美學站》官方粉絲團。未經授權, 請勿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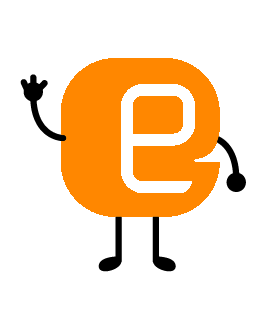


留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