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絲特從三歲開始就對許多主題發展出興趣,說得更精確些,根本是瘋狂著迷。一開始是迷恐龍,當然,許多孩子都對恐龍有興趣,但艾絲特的興趣之濃厚,常把旁人搞得精疲力竭,老實說這不太尋常。完全沒別的事能引起她的興趣,她畫恐龍、和恐龍玩、打扮得像恐龍。「我不是艾絲特,」她說。「我是暴龍。」每天晚上的睡前故事一定要和恐龍有關,所有對話多少都會牽扯到恐龍。西西莉雅才五分鐘就覺得無聊──牠們絕種了!有什麼好說的?幸好約翰保羅也對恐龍有興趣,還特地帶艾絲特去博物館、幫她買書,父女倆坐在一起好幾個小時,談著草食性與肉食性恐龍。
之後,艾絲特的「興趣」更包羅萬象,有雲霄飛車、海蟾蜍,最近還迷上鐵達尼號。現在她十歲了,能自己上圖書館或網路查資料,所收集到的資訊讓西西莉雅大感驚奇。是什麼樣的十歲小孩竟然能躺在床上,讀那些她只能勉強搬得動的磚塊書?
「要多多鼓勵!」學校老師這麼說,但西西莉雅有時不免擔心艾絲特可能有某種程度的自閉症。她擔憂地和母親提起這件事時,母親笑道:「可是艾絲特就和妳以前一模一樣啊!」才不是呢,這哪能和把芭比娃娃排得好好的相提並論?
「其實我有一塊柏林圍牆的石塊,」那天早上,西西莉雅突然想起這件事,便告訴了艾絲特,看著艾絲特發亮的雙眼,她也很開心。「柏林圍牆倒塌後,我去了德國。」
「我可以看看嗎?」艾絲特問。
「送給妳,親愛的。」
珠寶和衣服是給伊莎貝兒和波莉的,柏林圍牆的石塊呢,則是給艾絲特。
一九九〇年代,二十歲的西西莉雅曾與友人莎拉一同前往歐洲度假六星期,那時柏林圍牆剛垮幾個月。大家知道,莎拉這人優柔寡斷是出了名的,卻和果決的她成為完美旅伴,沒起過什麼衝突。
她們倆到了柏林,發現圍牆前面排滿觀光客,想用鑰匙、岩石或任何找得到的東西撬一塊圍牆上的石頭當作紀念品。柏林圍牆像是恫嚇這座城市的惡龍,如今觀光客和烏鴉一樣,啄走了牠的遺骸。
西西莉雅和莎拉沒有任何器具,無法撬下石塊,乾脆決定向當地人買一塊──好吧,是西西莉雅決定的,那些人很有生意頭腦,早早就擺好攤販售各種東西。資本主義果然贏了。無論是和彈珠一樣小的灰色碎石,還是連塗鴉一應俱全的大石塊,什麼都買得到。
西西莉雅不記得這個灰色小石頭到底花了她多少錢,說不定那是隨便從別人門前的花園撿來的。「搞不好喔!」那晚她們倆趕搭火車離開柏林時,莎拉如此說道。想到自己那麼容易受騙,兩人都笑了,但她們覺得自己至少參與了歷史。西西莉雅把她的小石塊放進紙袋,在上頭寫著「我的一小塊柏林圍牆」,回到澳洲後,她就把這紙袋及其他收集來的紀念品,例如杯墊、火車票、菜單、外國硬幣和旅館鑰匙,全扔進一個盒子。
西西莉雅多希望當初更留意柏林圍牆、多拍點照片、打聽更多趣聞,這樣或許就能和艾絲特分享。其實她對柏林之旅印象最深的,是在夜店親吻一個棕髮德國帥哥。他不停從飲料裡拿出冰塊抹著她的鎖骨,那時覺得這樣好撩人,但現在似乎只顯得不衛生、黏答答。
要是她是個有好奇心、關心政治的女孩,懂得和當地人聊聊住在圍牆陰影下的生活就好了。可惜她能和女兒分享的,只有親吻與冰塊的故事。伊莎貝兒與波莉會愛聽親吻與冰塊的故事,至少波莉會。伊莎貝兒年紀不小了,因此聽到媽媽親誰都覺得噁心。
西西莉雅把「找出柏林圍牆石頭給艾」,列入本日待辦事項清單(她已用iPhone的應用程式列出二十五項)。差不多下午兩點,她上閣樓去找。
其實屋頂下的儲藏空間很小,或許稱不上是「閣樓」。要到上面,得先從天花板的活板門拉下一道梯子。
上去閣樓後,她得彎腰駝背,免得撞到頭。約翰保羅絕不肯到閣樓,因為他有很嚴重的幽閉恐懼症,每天上班寧願爬六層樓,也不要搭電梯。這可憐的男人常夢到被關在房間裡,牆面不斷收攏,他會大喊「牆壁」,隨後滿頭大汗、眼神慌張地醒來。西西莉雅曾問他:「你小時候曾被鎖在櫃子裡嗎?」她不會對婆婆這樣做感到意外,不過他很確定沒有這回事。西西莉雅曾問她婆婆,但婆婆說:「其實約翰保羅小時候從來沒做過惡夢,睡得可香了,或許妳昨晚讓他吃得太豐盛了?」現在,西西莉雅已習慣約翰保羅做惡夢。
閣樓雖然又小又擠,但乾乾淨淨、有條不紊。這些年來,「有條不紊」似乎成了她的招牌特色,她就像個靠著這特點走紅的小小名人,有一陣子親友們很愛用這一點來評論與揶揄她。這習慣已根深蒂固,她的生活非常有條不紊,彷彿母職是種運動,而她是冠軍選手,她還在繼續思考:還能怎樣更上層樓?怎樣能在不失控的情況下,多擠出一點時間?
正因如此,其他人(比如她妹妹布莉吉特)滿屋子是積了灰塵的垃圾,而西西莉雅的閣樓卻堆疊標示清楚的白色塑膠整理箱,唯一不那麼「西西莉雅」的部分,是角落那高高疊起的一堆鞋盒。那些都是約翰保羅的,他喜歡把每個會計年度的收據放在不同鞋盒中,這習慣早在他遇見西西莉雅之前就已經養成。他對鞋盒沾沾自喜,因此她克制自己不要跟他說其實檔案櫃更能有效運用空間。
多虧整理箱標示得很清楚,她沒多久就找到柏林圍牆的石塊。箱子上寫著:西西莉雅:旅行/紀念品,一九八五——一九九〇。她一打開整理箱的蓋子,便發現褪色的棕色紙袋,這就是她小小的歷史之物。她拿出這石塊(水泥塊?)放在掌心,它看起來比印象中還小,雖然不特別令人稱奇,但願能換來艾絲特微揚嘴角,露出少見的微笑。要艾絲特微笑可得非常拚命。
之後西西莉雅讓自己分心一下看看這箱子──對,她每天要做很多事,但她畢竟不是機器,有時會浪費一點時間,嘲笑自己和那個用冰塊抹她鎖骨的男孩合照。他就和這一小塊柏林圍牆的石頭一樣,沒有印象中那麼了不起。電話突地響起,把她從過往回憶中拉回,她太急著起身,頭撞到了天花板,疼得要命。牆壁、牆壁!她邊咒罵邊往後退,手肘卻撞到約翰保羅的鞋盒堆。
至少有三個鞋盒的蓋子掉了,裡頭裝的東西像小山崩似地掉落。看吧,用鞋盒收納真的不是什麼好辦法!
西西莉雅再度咒罵,又揉揉頭,真痛呢。她看看鞋盒,發現都是一九八〇年代的會計年度。她動手將這堆收據塞進其中一個鞋盒,這時,她瞄到一個白色商用信封,上頭寫了她的名字。
她拾起這封信,認出那是約翰保羅的筆跡。
上面寫著:
給我的妻子西西莉雅
我死後才能打開這封信
她大笑,又突然停止,好像在派對聽見某人的話而捧腹大笑,卻赫然發現那不是笑話,而是很嚴肅的事。
她再看一遍信封上的字:「給我的妻子西西莉雅」,頓時雙頰發燙,好像很難為情似。是為他,還是自己?她不確定。那感覺像不小心撞見丟臉的事,比如撞見他在淋浴時自慰。米麗安曾逮到道格在淋浴時手淫,這種事情要是讓大家知道就太可怕了,但有一回米麗安兩杯香檳下肚就洩漏了這個祕密,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就不可能當作沒聽過。
裡頭寫了什麼?她差點當場拆信,但又怕像她有時(但不常)把最後一塊餅乾或巧克力塞進嘴裡一樣,良心會譴責自己貪吃。
電話再度響起。她沒戴錶,完全不知現在幾點。
她把剩下的文件全部塞回其中一只鞋盒,拿了柏林圍牆的石塊和那封信便匆匆下樓。
她才離開閣樓,忙碌的生活就像洪流般迎面襲來,把她沖走。有特百惠的大訂單要出貨、要去學校接女兒們、得去買條魚當晚餐(約翰保羅討厭吃魚,所以我們會趁他不在家時多吃),還有電話要回。教區神父喬打了好幾通電話,提醒她明天是娥蘇拉修女的葬禮。他擔心人數不足,而她說她當然會去。她把約翰保羅的神祕信件放在冰箱上。晚餐前,她把柏林圍牆的石塊交給艾絲特。
「謝謝,」艾絲特畢恭畢敬地接下這小石塊。「這石頭是從柏林圍牆的哪一段取下來的?」
「嗯,應該滿接近查理檢查哨的。」西西莉雅非常有自信地說,但其實根本沒概念。
但我可以告訴妳,那個拿冰塊的男生穿紅T恤搭白色牛仔褲,他以手指撩起我的馬尾說:「真漂亮。」
「值錢嗎?」波莉問。
「我很懷疑。怎麼證明這真的取自柏林圍牆?」伊莎貝兒問,「看起來不過是一塊石頭嘛!」
「檢驗DMA。」波莉說。這孩子電視看太多了。
「是DNA,不是DMA,而且人類才有DNA。」艾絲特說。
「我知道啦!」波莉每回學到什麼新知,卻發現姊姊們早已學會,就會惱羞成怒。
「好,那為什麼——」
「妳們覺得今晚『超級減肥王』誰會被淘汰?」西西莉雅問,同時不免開始想:唉,不管別人怎麼想,總之我不要再談現代史上偉大的轉捩點,雖然那可以給女兒來點機會教育。我要聊沒營養的電視節目,即使那沒有教育意義,卻能讓我耳根清靜,避免頭痛。要是約翰保羅在家,或許她就不必改變話題。有聽眾在的時候,她更有餘力當個好母親。
接下來的晚餐時間,女孩們都在聊「超級減肥王」,西西莉雅假裝有興趣,心裡掛念的卻是冰箱上的那封信。等餐桌收拾好,女兒都去看電視時,她就要把信拿下來好好瞧瞧。
現在,她放下茶杯,把信封拿起來就著燈光看,兀自輕笑。看起來像是手寫信,寫在有線條的筆記本紙上,但是看不出任何文字。
約翰保羅會不會是在電視上看到前往阿富汗的軍人寫信,要是陣亡,信就會寄給家人,像是來自墳墓的信,遂覺得依樣畫葫蘆也不錯?
西西莉雅無法想像他坐下來做這種事,那實在太濫情了。
不過也挺貼心的。要是他死了,他希望大家知道他多麼愛大家。
「……我死後。」為什麼他會想到死亡?他生病了嗎?這封信看起來是很久以前寫的,但他現在仍活得好好的。此外,他幾星期前才去做身體檢查,克魯格醫師說他「和種馬一樣壯」,接下來幾天,他就在家把頭後仰,像馬那樣嘶鳴,四處奔跑著,波莉騎在他背上,將抹布在頭上像鞭子那樣甩。
西西莉雅想起這回事,臉上浮現笑容,焦慮煙消雲散。所以,幾年前約翰保羅非比尋常地做了一件濫情的事──寫下這封信,那沒什麼大不了,她不該只因為好奇就拆信。
她看看時鐘,快八點了,約翰保羅快打電話回家了。他出差時,每天大概都在這時間打電話回家。
她甚至不會提起這件事,免得他不好意思,況且這話題並不適合在電話上聊。
不過呢,要是他死了,她該怎麼找到這封信?說不定找不到呢!他為什麼沒交給他們的律師,也就是米麗安的先生道格.歐本海莫?每次想到他,就很難不聯想到他在浴室幹了什麼,當然這不妨礙他身為律師的能力,只不過洩漏出米麗安的床上功夫(西西莉雅和米麗安有點愛較勁)。
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現在不是對床上功夫洋洋得意的時候。停,別去想性那件事。
總之,約翰保羅沒把這信交給道格,這實在太愚蠢,要是他真的死了,容不下一絲凌亂的她或許哪天衝動,看都不看一眼就把所有的鞋盒扔掉了。約翰保羅隨便把信塞在鞋盒裡,怎能奢望她找得到?
為什麼不放到收藏遺囑副本、壽險保單等資料的文件夾?
她所認識的人中,約翰保羅算得上是最聰明的一個,卻是個生活白癡。
「說實在,我不明白為什麼男人可以統治這個世界。」她今早和妹妹布莉吉特聊到約翰保羅在芝加哥把租車的鑰匙搞丟時如此說。西西莉雅看到他傳來的簡訊時差點沒瘋掉,她根本束手無策!雖然他不期望她做什麼,但還不是一樣!
約翰保羅經常出這種紕漏。上一次出差時,他是把筆記型電腦忘在計程車上,這男人老是遺失東西,皮夾、手機、鑰匙、婚戒,什麼都不翼而飛。
「他們很會蓋東西,」她妹妹說。「比如造橋鋪路。我是說,妳連小屋都不會蓋吧?陽春的小泥屋?」
「我會蓋小房子。」西西莉雅說。
「妳搞不好真的會耶,」布莉吉特哀嘆道,彷彿例子舉得不好。「反正呢,這世界不是由男人統治的。我們的總理是女性,而且妳也掌管了妳的世界,掌管了費茲派翠克家、聖安琪小學,還掌管了特百惠的世界。」
西西莉雅是聖安琪小學家長與公民協會的會長,也是澳洲排名第十一的特百惠顧問。她妹妹覺得這兩個角色實在可笑。
「我才沒有掌管費茲派翠克家。」西西莉雅說。
「最好是沒有啦!」布莉吉特大笑道。
如果西西莉雅死了,費茲派翠克家族就會……嗯……很難想像會發生什麼事。約翰保羅不只需要她留下一封信,他需要整本手冊,包括這房子的平面圖,說明洗衣間和櫥櫃的位置。
電話響起,她趕緊接起。
「我猜猜看,女兒正在看胖子的節目,對不對?」約翰保羅說。她一向喜歡他在電話上的聲音,低沉、溫暖而舒緩。沒錯,老公實在沒救,老是姍姍來遲、丟三落四,但他還是秉持傳統觀念,負起照顧妻女的責任,一副「我是男人,這是我的天職」的模樣。布莉吉特說得沒錯,西西莉雅掌握了自己的世界,但她知道若發生危險,例如瘋子持槍掃射、洪水、火災之類,約翰保羅會搶第一來拯救她們的生命。他會擋在子彈前、會造竹筏,更會把她們安全帶離熊熊烈火,等擺平一切之後,他又會把主導權交回給西西莉雅,拍拍口袋說:「有人看到我的皮夾嗎?」
目睹小蜘蛛人死亡後,她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約翰保羅,手指按按鍵時都在發抖。
「我找到一封信。」西西莉雅說,指尖畫過信封正面的手寫字。她一聽見他的聲音,就知道自己會問起這封信。他們已經結婚十五年,彼此之間沒有祕密。
「什麼信?」
「你寫的信,」西西莉雅說道,盡量一派輕鬆幽默,這樣情況就不會失控,無論信裡寫什麼都沒有意義,也不會改變什麼。「你寫給我的,說你死了才能拆封的信。」對先生說出「你死了」這幾個字,聲音不可能保持正常。
接下來是一片靜默。一時間,她以為電話斷線了,只是她仍聽得見聊天聲與碗盤聲,聽起來他是在餐廳打電話。
她的胃一陣緊縮。
「約翰保羅?」
(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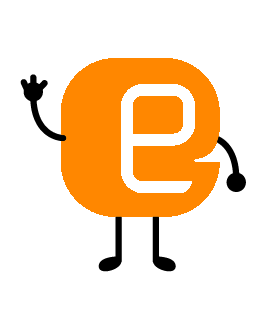


留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