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華人的歷史,正式記錄最早可追溯至一八五四年,當時第一批華工約七百人坐船來到巴拿馬,參與修築巴拿馬鐵路。自此一批又一批的華人來到巴拿馬工作,部分則定居下來,做起小生意、成家立室,並以巴拿馬為家。到今天巴拿馬這個拉丁美洲小國,有約百分之五的人口是華人;若把有華人血統者也算進去的話,更估計高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華人在巴拿馬的故事,其實正是一個個離鄉別井、追尋更好生活的故事。
來到巴拿馬城,經朋友介紹下,住進了Terry和Wendy兩夫婦的家。他們住的是兩層的獨立屋,屋苑(由獨棟房屋組成的集合式住宅)位於巴拿馬城內華人聚居的中產地段,附近住的百分之八十都是華人;我住進去之後的第一餐,就是Wendy親自下廚的香港道地中菜,美味非常,叫我這個多月未嚐真正中菜的人吃得欲罷不能。
Terry和Wendy都是香港人,八年前透過Terry居於巴拿馬的兄長介紹,帶著女兒移居巴國;本來是髮型師Terry到了巴拿馬後改行做汽車零件生意,幾年下來,生活在當地算是不錯。香港人移民巴拿馬,聽起來似乎罕有,可是事實卻不然──在我遇過的巴拿馬華人當中,大概有一半曾在香港居住過,由數月到十數年不等;因此香港對於巴拿馬華人來說,多有一種親切感覺。
我在巴拿馬城逗留了接近一個月,本來學過的西班牙文大大倒退,因為在這個月中,我幾乎只說廣東話──這實在是非常特別,走遍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國語/普通話都是主要的語言,可是在巴拿馬大家卻開口都是說廣東話。那是因為現時巴拿馬估計有十三萬華人,當中竟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來自廣東省一帶,所以都以廣東話作為主要語言。他們當中來自廣州花縣的人數最多,約占百分之七十,其餘的多來自恩平、開平、台山、新會、中山等。為什麼一個小小花縣的移民會占上整個巴拿馬華人的大部分?這大概與華人移民的模式有關:典型的移民故事是先有人來到了巴拿馬,工作五年還清了債項,然後開始自己的生意,多數為食肆或小型超巿;到站穩陣腳了,便把鄉間親人的子侄申請過來──年輕人來到巴拿馬之後,又再開始同樣的故事。如此一個帶幾個,漸漸花縣的移民便以幾何級數上升,成為巴拿馬華人的主流。反而與巴拿馬政府有邦交關係的臺灣,在巴拿馬的僑民只有約三百人。
香港人在巴拿馬
傅振琪是另一個我在巴拿馬遇上的香港人,他的家族四代都與巴拿馬結下不解之緣。傅先生現時五十多歲,早於外祖父一輩已移居巴拿馬,母親則在一九二七年在巴拿馬出生,七歲那年隨父母回到香港,一直在新界與離島以務農為生;傅先生五兄弟都在香港出世,傅振琪生於長州,懂事後便一直幫家裡種田,沒有上過學讀過書。直到他十九歲,那年是一九七八年,便決定跟隨兄長的步伐,到巴拿馬尋找機會。
沒有讀過書的傅振琪,來到巴拿馬之後一邊慢慢學西班牙文,一邊做著不同的工作。他做過餐館、酒莊等,後來還開了自己的麵包店。這其實是很典型的在巴華人生活──努力工作、儲錢開店,生活也漸漸進入小康。許多華人都跟我說,在巴拿馬只要勤力工作,不染上賭錢惡習,要好好生活甚至發達並不困難。
工作之餘,傅振琪也成家立室。在巴期間他回到香港,認識了後來的太太,並帶她來到巴拿馬定居,生下了四個女兒。但夫妻二人也有想過,到底應留在巴拿馬還是香港?九八年時,太太就帶同三個女兒回到香港居住,住了一年多,但傅振琪實在太掛念她們,於是回到香港把她們都接回來;就此,確定了巴拿馬將是一家人安身立命之地。
傅先生拿出一張全家福給我看,是他五兄弟和家人子侄的合照。五兄弟和母親都先後來到巴拿馬定居,兄弟在巴拿馬結婚生子,子侄也在這兒成家立室;家人中有華人、有拉丁美洲人、也有中巴混血兒,一家人早就融入了巴拿馬社會。然而傅振琪仍希望女兒們不要忘記自己的根,曾在香港居住過的她們都懂得中文,能讀能寫,每星期也會上中文的基督教教會聚會,在巴拿馬新一代華人中,許多人的中文能力都遠不及她們。
文化傳承
巴拿馬的華人如何傳承中國文化?因為這個問題,我認識了Emilitza。Emilitza是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已在巴拿馬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與傅振琪一家上同一所華人教會。她是虔誠的基督徒,身兼兩職:既打理巴拿馬唯一一間華文教會書店──晨光書房,也協助身為校長的丈夫,負責統籌仁愛書院(巴拿馬其中一間華文學校)的華文和西班牙文課程,自己也會向華人新移民教授西班牙語。
晨光書房是我在巴拿馬見過的唯一一間正式的中文書店,店內除了販售中文書籍外,還有英文和西班牙文書;書種除了宗教書籍,還有小說、雜誌、以及字典和學習語言的工具書。Emilitza自十三年前開始負責打理晨光書店,雖然生意不算很好,但總算是有一個文化基地,讓有興趣學習中文的人有一個尋找資源的地方。許多在巴華人雖然都已在巴拿馬落地生根,但也如傅振琪般希望下一代可以懂得中文,一來因為那是自己的根,二來也因為中國經濟越益強大,懂中文也代表有更多發展機會。然而移居巴拿馬的華人普遍學歷不高,許多來自農村,本來就識字不多,因此閱讀風氣不盛;雖然希望下一代可以學會中文(特別是國語),但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其實殊不容易。
許多華人團體都有開辦中文班,但最正統的方法,始終是讓孩子在學校學習。據記載,巴拿馬最早的華人學校名為永興小學,早於一九三三年成立,在巴拿馬城的舊唐人街附近,初時規模只有兩位教師三十名學生。而現時巴拿馬歷史最長的華人學校則是中巴文化中心,開辦了差不多三十年,現時有一千七百多名學生,由幼稚園到高中都有,我在巴拿馬認識的許多華人朋友都曾在這兒讀書。陳中強是中巴學校的現任校董,已故的父親陳奉天則是學校的創辦人;陳奉天於一九二七年來巴,以製衣廠起家,後來事業有成,並成了巴拿馬的華人領袖。上世紀八○年代,陳奉天與其他華人一同集資創辦了中巴文化中心,教育在巴華人的下一代。
我問陳中強,學校除了西班牙文外,教的是什麼語言和文字?原來學校素來與臺灣政府交好,學校也一直教授繁體字;而語言方面,以前曾經用廣東話教學,現在則改為用普通話,除了因為普通話實用層面較廣外,也由於缺乏教授廣東話的老師和教材。但是陳中強和Emilitza都承認,巴拿馬學生學習普通話其實並不容易,由於生活上沒有人跟他們練習,所以往往事倍功半。
發聲吶喊
海外華人都有個共通點,就是但求安居樂業,少介入當地政治。對於公共事務,即使影響到自己,也通常逆來順受、或隨機應變,多數不會高調反對抗議;如果真的受不了,寧願用腳投票,乾脆離開,再另覓地方安身。就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巴拿馬的種族主義風大盛,不少華人就在那個時候離開了巴拿馬。在巴華人齊心站出來高調抗議,歷史上大概就只有一次,也不是很久之前,只不過是二○一一年,三年之前。
這次行動的其中一個核心人物是羅銀洲,由於他是該地多個同鄉會及華人團體的組織者,於是親身見證了這次事件。羅銀洲祖籍赤溪,十二歲來到巴拿馬,但祖上三輩均在巴拿馬工作及居住(曾祖父估計在十九世紀末已來巴拿馬打工),算是第四代巴拿馬華人。兒女都在巴拿馬出生,現時已移居美國,但他認為巴拿馬生活較好,不願隨兒女移居。他在巴生意有成,多年來亦積極參與華人社團的工作。
提到二○一一年的事件,他滔滔不絕地相告當時的情況。當時巴拿馬一個小城巿喬雷拉(La Chorrera)發生了轟動全國的連環兇殺案,五個華裔年輕人先後被綁架失蹤,後來發現全被殺害,舉國關注。這反映了當地治安的嚴重問題,華人團體於是聯合起來組織行動,由本地的華人團體連結全國的華人團體,最終決定於九月二十一日那天在喬雷拉巿發動大遊行。當日參與的人出乎意料地多,估計數以萬計,而且當中許多都是巴拿馬本地人;參加者穿上白色衣服,靜默遊行以悼念五名死者。當日以及後來表態關注事件的,更包括了巿長以及後來當選的巴拿馬總統等。團體更發起了全國罷巿向政府施壓,是當地華人歷史上的首次罷市行為,也得到了巴拿馬人的普遍支持和同情,顯示了華人已經融入當地社會,亦反映出雖然這次被殺害的是華裔,但治安問題同樣也是全國人民的切膚之痛。
只是綁架案雖已過了三年,巴拿馬治安卻並不見有所好轉,然而對於在巴華人而言,只要情況尚可忍受,巴拿馬始終是他們安居樂業的家。
---本文摘自《旅行是一場修行》一書,時報出版。
移動讓人了解世界的不同,孤獨叫人認識自己的內心。
一次好的旅行,是使世界更美好的一場修行。
旅人踏上路途,可會幻想自己是個孤獨的修行者?在獨自上路的過程中,學習到如何與自己獨處,或靜或動,或放聲高歌,或任思緒恣意縱橫。
透過責任旅者的行腳,我們看見旅行的另一種可能。
旅行二十二個月,走過四十餘個國家和地區,旅者用文字寫下遠方人們的生活、記錄另一個國家的榮辱:從華沙到紐倫堡,走訪二戰帶給歐陸的歷史傷口;進入 戰火蔓延的巴爾幹半島,恐懼與轟炸遺跡隨處可見。比鄰美國的墨西哥,是懷抱美國夢的偷渡者所必經的中途站;中美的巴拿馬則是一部活生生的華人移民血淚史。 來到古巴,探訪切?格瓦拉的革命之路;走進祕魯,在馬丘比丘之前思考文明的興衰如潮汐。
繼《旅行在希望與苦難之間》中林輝從亞洲走到中東,看過世界的希望與苦難後,他接著來到了歐洲和中南美洲。看過去,也看現在;看別人,也看自己。玄妙的旅程似要告訴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越深,越有可能將善念化為行動。
理解世間的苦難,奉獻一己之力改變世界,旅行也是修行。
【本文出處。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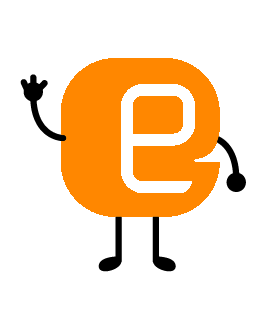


留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