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嘉年華》導演文晏
有人將《嘉年華》形容為一部「社會問題電影」,其中的誘姦、員警與官員的勾結、傷勢鑒定單位被買通、動用金錢權利封口等問題之深入與敏感,讓人對導演文晏的勇氣佩服至極。不過,文晏卻說,「揭發黑幕」並不是她要呈現的重點。因為生活在一個粉飾太平的虛幻世界裡,現實生活中會發生的事,似乎永遠會超出我們的想像,不斷刷新人們認知的底線。 然而,「我們有盡一名旁觀者應該盡的責任嗎?我們是否在消費這些事情?尤其是對受侵害者,我們又是否給予過她們真正的關心?」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在做什麼?這是文晏特別想反思的一件事。因為社會上有太多的憤怒,卻只有太少的思考。
因此在電影《嘉年華》中,並沒有對侵害案件的直白呈現,沒有當事人的慘烈痛苦,也不特別刻畫加害者,甚至涉事官員都沒有露過正臉。反而是目睹案件發生經過的旅店櫃檯人員的沉默、被侵害女孩母親的二次暴力、婦檢醫生的冷漠等,更加讓人難過。
文晏說,電影中每一個角色都是一種境遇的反映,明哲保身在我們這個時代非常常見,她希望觀眾不要只是停留在討論這個人好與不好,而是去想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是怎樣的社會造就了他們。其實,他們並不是特例,都是我們生活中極普通且真實常見的人。「我更想探討的是,在這些事件發生後,我們是如何失職,尤其這些在逆境中的女孩如何成長?如何面對社會?她們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並不會因為這類案件的辦與不辦而改變、停止,傷害也從沒停止過。」
問:為什麼這個社會容不下瑪麗蓮夢露?
答:因為社會對女性的偏見仍四處充斥著。
問:《嘉年華》故事發生在一座海邊小城,裙角飛揚的瑪麗蓮夢露雕塑是這城市的著名景點,剛才你談到了偏見,片中瑪麗蓮夢露雕塑的建立與拆除也涉及偏見嗎?
答:對,瑪麗蓮夢露雕像是我在寫劇本過程中讀到的一則新聞,在中國廣西一個小城,建造了一座號稱是世界上最高的瑪麗蓮夢露雕像,但6個月後被拆除了,因為裙襬飛得太高了。我覺得這事件跟我這個故事很契合,一見到瑪麗蓮夢露,大家就說是性感尤物,所以注視她的目光也都是充滿誘惑的、撩撥的。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瑪麗蓮夢露可能跟我們一樣,只是一個在尋找自我、尋找幸福,希望能夠主導自己人生的女性。
雕塑拆除的時候,當地女孩非常留戀。對於十幾歲的女孩而言,她們可能會覺得這就是一個美麗的阿姨,將來我希望像她一樣美麗。或者對於更小的像小文(片中被侵害者)這樣的女孩來說,她可能會覺得她好像我的媽媽。
她們其實只是用非常單純的目光在注視瑪麗蓮夢露,跟世俗的偏見有著極大的反差,我正想在電影裡表現這種反差。
問:正因偏見,瑪麗蓮夢露雕像在片尾被拆除了?
答:對,與其說我們社會容不下這樣的女性,不如說這意味著像類似的問題永遠沒有獲得解決。在真實生活中這樣的雕像也會被拆除,也會覺得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有傷風化的,我們要把它藏起來放在一個角落,代表了對女性的偏見在今天依然是充斥著的。
問:侵害兒童案件時有發生,這是否刺激了你拍攝《嘉年華》?
答:我是2014年開始寫《嘉年華》的,當時《白日焰火》已經上映(文晏是該片製片人),我才得以靜下心來寫劇本。我關注這一類事件挺長時間了,一方面是情感上過不去,看見會非常難受;另一方面,它會引起我的思考,為什麼這類事情這麼多?而社會要做什麼來幫助這些孩子?
其實不光是孩子受到侵害,還有很多少年在很年幼時就參與犯罪,為了一些很小的原因,去做不該做的事情。也許是現在發展太快了,成年人都很忙,我們的注意力都在別的地方,反而忽略了對孩子的教育和保護。
這可能是一個比想像中要更嚴重的事,現在它已經呈現出來,未來或許會引發更大的問題,這才是讓我開始想講一個少女故事的原因。
問:對於侵害案件,片中這個家庭「為了孩子的名聲」選擇了妥協,這可能也是現實中很多家長會做的選擇,你怎麼看?
答:這正反應了社會的問題。原本加害者應該是可恥的,受害者是無辜的,但現在我們對於受害者的羞恥感,卻比什麼都強。倘若你被人捅了一刀,大家不會說你好可恥啊,但是為什麼孩子受到侵犯,反而要遮要躲,覺得羞恥,這是一個極大的偏見。如果我們能夠消除這樣的偏見,能有優良的機制,無論是學校還是心理機構,真正幫助到這些孩子,家長就不會做那樣的選擇。
問:韓國電影《熔爐》和《素媛》對你的創作有影響嗎?
答:我光看社會新聞,感受就已夠強烈的了。
問:女童受害後,片中有一個婦科檢查的主觀鏡頭特別狠,這是怎樣考慮的?
答:這就是我們社會給予孩子的暴力。有人開始還會問我,為什麼這個加害者沒有著重描述他,連正臉都沒有,現在大家慢慢都理解了,因為一次暴力不是最可怕的,旁觀者的冷漠、消費,甚至二次傷害才更可怕。
最近總有人問我看沒看過《熔爐》、《素媛》,其實我根本不用看那些,我自己作為一個社會旁觀者,感受就已經很強烈了。最初看到這樣的社會新聞我很難受,但又發現所有的事情都難以找到解決的出口,思考了很久,直到看到一個女孩看監控視頻的畫面,我才找到了一個旁觀者的切入點,因此設置了雙女主的結構,一個當事人,一個旁觀者,而她們之間其實是可以互換的,我們卻往往意識不到這一點。後來得知瑪麗蓮夢露雕像的事,不斷在我腦海中閃現,就一點點加進去了。
問:說到二次傷害,片中的小文被侵犯後,她媽媽非但沒有安慰,反而惡語相向,甚至剪掉了女兒的頭髮。爭吵過後,小文沒有拿洋娃娃或者其他一些能帶來慰藉的東西,卻抱走了她養的金魚,這點也讓人動容。
答:對,在某個影展上,前亞太電影大獎的主席,就特別喜歡周美君飾演的「小文」,他跟我說,你沒有把受害人描繪成一個常規的受害人,讓大家可憐她,看到她就掉眼淚。反讓小文的個性有點小倔強,是個堅強的小靈魂,這樣更能打動人。要大家去可憐一個孩子太容易了,而我想表達的是,《嘉年華》片中每一個女性都是有靈魂的。
我之前在國外念書,國外對女性問題的探討比較多,也較開放。但在國內,我經常觀察周遭的女性,她們的幸福感相對是少的,焦慮也很多。我常在思考這個差異。這就是為什麼《嘉年華》並不只是講性侵這個話題,而是還有其他女性角色,她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有著不同的處境,也面臨著各式各樣的壓力。
譬如劉威葳所飾演的小文母親,她是個不快樂的女人,婚姻失敗給她的打擊非常大,讓她的自信蕩然無存。當女兒發生了這樣的事,她卻帶有強烈的羞恥感,幾乎忘記自己是母親的角色,只覺得作為女人的羞恥。
在某種程度上,片中這些女性角色是可以互換的,小文可以成為下一個小米(文淇飾演的旅店櫃台員、目擊者),小米可以成為下一個莉莉(墮胎的旅店櫃員),莉莉則有可能將來成為一個母親。
問:有人評價這部電影中的女性是絕對主體,男性有些是施暴者,有的則特別懦弱,這是你有意為之的嗎?
答:其實不是,這些人物都來自於真實的生活。我講的是人的遭遇,沒有劃分男性或女性,女性有像小文的媽媽、去墮胎的莉莉,她們都有認知上的局限和各自的問題。我並沒有刻意要表現男性怎樣。
又例如像旅店的經理,他就是一個明哲保身的小人物,在我們社會裡特別普遍。又像莉莉的男友小健,你說他像個壞人吧,但社會上就有很多這樣的男孩子,他為什麼成了這樣?其實我們應該反思,究竟是怎樣的社會造就了這些人,而不是簡單地說這個人好、那個人壞。
問:審查是否影響了《嘉年華》的結尾處理?
答:電影能跟觀眾見面最重要。
問:電影給了一個光明的結局,是因為審查嗎?在現實生活中,總會有施暴者沒被繩之以法,事件最後不了了之…
答:是的,但這並不重要。我講的是這些孩子在成長中面臨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並不會因為案件的結與不結而改變、停止,傷害也從來沒停止過,社會的各個層面,並沒盡到該盡的責任。
倘若大家想在中國看到這樣的電影,你必須用一個巧妙方法,讓大家能看到。如果你真的仔細聽了片中那段廣播,就會意識到電影並沒有停留在圓滿的結局了,而是還有別的聲音。大家所謂的光明結局,對我而言一點都不光明。
問:但結尾文淇飾演的小米騎車出走很有力量,雖然身旁是呼嘯而過的大卡車,運走了被拆掉的瑪麗蓮夢露…
答:對,我們從不會知道前途是否光明,但你只要有勇氣做出選擇,就是邁出的第一步。我想留在這樣一個點上,因為這個問題不是簡簡單單某一個人、或者某一方面改變了,就可以徹底解決的,而是需要每一個人去反思的。這條路肯定漫長,但大家都在等,等著你去改變。
問:對你來說,《嘉年華》的片名意味著什麼?英文名《Angels Wear White》呢?
答:「嘉年華」字面上有美好年華的意思,這些少女處在人生最美好的年華,但我們卻把本來屬於她們的嘉年華給剝奪了,我們成天像在狂歡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完全忽略了下一代。
「嘉年華」直譯成英文只是狂歡節的意思,也就聯想到了「穿白衣的天使」,當我們在探討女孩子的純潔問題,但難道被侵犯就不再純潔了嗎?這種不該有的羞恥感,至今仍在助長類似事件不斷發生,就因為你不敢啟齒。這是一個很虛偽的枷鎖。
問:《熔爐》等電影推動了韓國立法,你希望《嘉年華》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答:我並不寄望用一部電影來改變社會,改變社會在於每一個人、每一天的所作所為。如果這電影觸動了你,給了你一些啟發,我希望你能夠在人生中做一點什麼事,這些細微的、看似不起眼的舉動,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有力力量。
(摘自時光網專訪)
相關影音:第54屆金馬獎 最佳導演獎 文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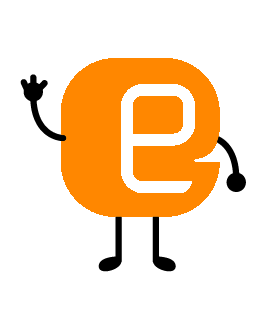


留言評論